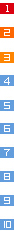|
携孙辈回乡 实地感受文化根源
“爸爸妈妈,我今天把妻子、女儿、孙女、外孙女都带来了,来看您老人家!”2016年7月4日,山东菏泽高孙庄,81岁的台湾老兵高秉涵在父母的坟前,反复叮嘱孙女们,要永远记住这里是自己的“根”。
高秉涵:一共四个孙女,我有生之年,想让她们回来,认识认识姥爷的根在哪,爷爷的根在哪。
出生在山东菏泽的高秉涵,13岁的时候随老乡前往台湾,56岁第一次踏上回乡的旅程。很多人对这位老人的了解来自于中央电视台2012年度感动中国的颁奖现场。
“海峡浅浅,明月弯弯。一封家书,一张船票,一生的想念。相隔倍觉离乱苦,近乡更知故土甜。”这是感动中国组委会为2012年度“感动中国”人物——高秉涵授予的颁奖词。从台湾当局开放居民到大陆探亲以来,高秉涵受一些老乡的临终嘱托,陆续将台湾老兵的骨灰带回家乡安葬。20多年来,他先后义务将100多位台湾老兵的骨灰带回了大陆老家。
高秉涵:在我心目中,老哥你们还活着,并没有死。我抱的虽然是你们的遗骨,但是如感动中国的最后一句话一样,我抱着一坛又一坛,不是老兵的遗骨,而是满满的乡愁。
正是因为装着满满的乡愁,对于高秉涵他们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来讲,回家,就成了天大的事情。高老说,这些年两岸交流频繁,他每年至少要回大陆两次,一次是春天,一次是秋天。春天是作为儿子,回来祭奠自己的父母;而秋天,则是到曲阜参加祭孔大典。但今年,他却把回家的日子改到了7月份。
高秉涵:趁暑假期间,带孙女们回来。因为她们没有到大陆来过,她们更没有到我的故乡菏泽来过。(想让她们)认识认识中国的文化,到黄河看看,看看孔林、孔庙,到泰山,水浒里的梁山。
记者:这些东西都是她们的课本上,或者她们的教材?
高秉涵:都有。
记者:都有和实际看,您觉得有什么不一样?
高秉涵:她们认为那是中国的,好像跟台湾没关系。刚才济南市的电视台跟着我,记者问10岁的外孙女“你是中国人吗?”她说“我不是,我爷爷是中国人,我是台湾人。”
记者:您听到她的这个反应,您什么反应?
高秉涵:我就是心里面很苦,很苦。
记者:苦?
高秉涵:因为我现在感觉到有点无力感,因为她们这四个人,可以说都是现在的小台独。
记者:我有点想不通,高老先生,您这一辈子,心都在找自己的故乡,不仅心在找,您也在用行动在找。您是她们的爷爷,姥爷,怎么可能在您家里面,自己的孙子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?
高秉涵: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化台独,这个太厉害了。
原本高老希望等孙辈再长大一点,懂事之后,再回故乡,但形势并不随他所愿。因此他把这一计划提前到了今年的暑假。
高秉涵:我希望能带她们回来,认祖归宗。我多讲几句,自从李登辉去中国化,蒋经国死了以后,李登辉去中国化,然后李登辉又连任了八年,接着陈水扁,这个将近20年的时间,去中国化很明显。原来的是中国地理,中国历史,这其中包括台湾地理、历史,台湾是中国的一省。但是他把它分开,中国地理,台湾地理,把中国地理列入外国地理。
记者:但是您没办法?
高秉涵:像这个情形,孩子都是一样。没有读书的时候,父母讲的是真理,一上了小学以后,老师讲的是真理,书本上讲的是对的。
记者:您有没有在家里面争过,告诉孩子们台湾是整个祖国的一部分?
高秉涵:争不过,没办法,孩子们说爷爷说得不对,书上说的是对的。
记者:您有办法吗,在您的家里这个小范围内,您有办法吗?
高秉涵:我没办法改变,我已经无能为力。现在投票给蔡英文的,就是那二十年开始的那些小台独的票,集中起来的。
正因为如此,高秉涵下决心要带着孙辈们回到自己的家乡,感受文化的根源。为此,这次暑假之行中,他首先安排孙辈们回菏泽老家扫墓祭祖,之后又带她们看了黄河、拜了孔庙、登了泰山。
高秉涵:台湾本身没有文化,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,它本来的文化,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,但是现在他们书本里面怎么教的,我们的老祖宗尧,舜,禹,周公,一直往下传过来,民进党教的东西,认为台湾老祖宗就是原住民,原住民是台湾的老祖宗,就是山地人。
记者:可是您觉得,您一己之力,带着几个小孙女,能改变什么呢?
高秉涵: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,我只是尽一个匹夫的责任而已。我这次来的重点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,一个是认祖,一个是消独。那个独是台独的独,要消除台独,消除我小孩的中毒。
记者:您带着孙女到济南看看济南的情况,再回到菏泽,看看菏泽老家,您觉得对孩子有没有影响?
高秉涵:现在没办法完全看到效果,她们唯一说的是爷爷真伟大。为什么?因为有二十几个记者,从7月3日我下飞机一直跟到我昨天。
记者:爷爷是个人物?
高秉涵:觉得爷爷是一个人物。
记者:还有?
高秉涵:另一个她认为中国人很厉害。因为在她们的小脑子里边,中国很糟糕。为什么?台湾的媒体一直播大陆是最坏的,好的不提。
记者:其实我理解您的意思,并不指望这一次能够改变什么,但是可能这一次会让她们有这种认识上的改变?
高秉涵:我认为这个改变不是马上看到的,但是我的目标是让她们知道,爷爷、外公生命源头在这里。
“母亲临走时告诉我两句话:你要活下去。母亲等你活着回来。”
菏泽是高秉涵出生长大的地方。他忘不掉1948年的那个清晨,十三岁的他离开母亲,离开家乡的场景。当时,身为国民党的父亲在战乱中去世,母亲担心时局更加动荡,决定让高秉涵去投奔设在南京的“流亡学校”。临行前高秉涵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响头,母亲拧着耳朵叮嘱他,如果学校解散,要一直跟着人流走,要活着回来。
高秉涵:母亲临走的时候,告诉我两句话,一个是你要活下去,一个是母亲等你活着回来,就是这两句话。
记者:她不会觉得再也见不着面了?
高秉涵:对,她认为大概见着面的机会不多了。
记者:她意识到了?
高秉涵:她意识到了。
记者:但是您没意识到?
高秉涵:我当然不知道,我这个时候因为年少,不知离别。母亲看穿了,国民党大势已去,但是她要我多活几年,叫我赶快走。
不知离愁的少年,离开了母亲温暖的羽翼。在南京“流亡学校”,高秉涵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,就不得不开始逃亡的生活,他杵着一根木棍,始终按母亲说的,跟着人流,努力求生。
记者:您是跟着什么人在走呢?
高秉涵:跟着逃难的难民群。
记者:你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?
高秉涵: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台湾在哪里。
记者:您一个人,那么小的一个小孩,跟着谁走,也不知道目的地,这路上出现什么情况,谁管?
高秉涵:没有人管,没有人管。
记者:不知道前途在哪?
高秉涵:对。
在混乱的逃亡人流中,他的双腿被别人手中滚烫的热粥泼伤,伤口反复腐烂生蛆,时隔六十年后,大块黑色的疤痕仍然附着在腿上。经过六个月的跋涉,十三岁的高秉涵跟着大批流浪的人,来到厦门的海滩,被人流裹挟着,上了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船。
记者:真挤上船的时候,想什么呢心里头,能不能回来,害不害怕,能不能回头?
高秉涵:我一开始流泪,后来掉泪没有人同情你,所以我就不掉泪。因为我发现我随时可以死,我在死和活之间的缝里挣扎,所以已经没有怕的感觉。
记者:这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子来说能适应吗?
高秉涵:如果我不走,我不忍,我不往前冲,就是死路一条。
在海上漂流数日后,高秉涵随逃亡人流到了台湾。举目无亲的他睡在台北火车站,跟垃圾场里的野狗打架,争抢别人吃剩的东西,
卑微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。
记者:您这三个月,跟猫狗抢食,在垃圾场跟猫狗抢食,您有没有心疼过自己?
高秉涵:没有,我想大概你们体会不到,一个人,我可能随时可以死,但是我在死里求生的时候,没有想到那些,不流泪了,也不可怜自己。你可怜自己,没有人同情你。
与猫狗抢食吃了三个多月之后,高秉涵受一位好心的老先生指点,成了台北火车站站台上的一名小贩,虽然收入很低,但终于有了活下去的希望。当时动荡的生活夺走了他大部分的行李,但因为母亲的嘱托,他始终随身带着小学师生毕业照,和初中新生录取证明,靠着这份证书,高秉涵一边劳动维持生计一边攻读了中学,之后又有机会考上了台湾“国防管理学院”法律系。
寄不出的思乡信 每一封中都写着“娘我想你”
记者:这段时间,你抱着过一段时间就能够回到菏泽去看妈妈的愿望吗?
高秉涵:那时候已经没有希望了,已经知道没有希望了。
记者:你知道见不着妈了,那时候肯定不通信,你会写信吗?
高秉涵:有写信,也写,写了就撕掉了。因为这个东西,那时候别人不能看到。
记者:您知道这个信寄不出去,甚至写下来被人看见都会有麻烦,那干吗还写?
高秉涵:这是一个疏解,想家时唯一能做的办法。
记者:您都写什么?
高秉涵:每封都会存在的,娘我想你。
记者:但是写的时候知道娘也收不着,自己写完了还得撕,这心里得多难受?
高秉涵:对,我写了以后,心里边就比较……
记者:痛快了?
高秉涵:痛快一点。
与绝大多数撤退到台湾的人一样,高秉涵最初以为这个小岛只是一个临时遮风避雨的住所,用不了多久,就能回大陆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,接下来的等待格外漫长。他在台湾当兵、做法官、干律师,靠着自己的努力成家立业、娶妻生子。然而即使这样,他还是惦记着家乡,惦记着家中的老娘。他说,那段时间他经常在夜里梦见自己变成了海鸟,飞过大海,回到了故乡。
记者:不都说娶了媳妇儿,忘了娘,您娶了媳妇儿,是觉得忘了娘了,还是觉得这个娘在心里边越来越更放不下了?
高秉涵:娘我还忘不了,我是从来不过生日。
记者:为什么?
高秉涵:因为我母亲生我那一天,是母亲的大难日,母亲拼命生下了我,那时候难产,没有西医,危险,所以我不过生日。
再后来,高秉涵发现回家无望的时候,他便开始拼命地把家乡的每一个记忆,变成文字,写在日记本上。
高秉涵:我就记我家的人,事,地,物,小草,动物,我都记。记我家的人,记我的老娘,我的外婆,我的奶奶,奶奶叫什么名字,姓什么,她娘家是哪的人。
记者:您是不是也怕忘了?
高秉涵:对,我就是怕忘了,我把这个交给我的儿孙,知道家乡的情形。好,我隔壁是二公爷家,二公爷有几个孩子,大孩子叫什么名字。
记者:您干吗把邻居也写上?为什么?
高秉涵:凡是我们知道的,我都写,我的瓜有西瓜,冬瓜。
记者:不只亲戚,还有瓜?
高秉涵:对,什么都写。
高秉涵拼命地记,就好像给自己家拍照片一样,日记本摞在一起足足有半米高。然而老天弄人,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了高秉涵珍藏日记的房间。日记毁了,思念依旧。1979年8月,高秉涵利用前往西班牙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,终于寄出了他离别母亲30年之后的第一封家信,信的地址和收信人是“山东菏泽,西北35里路,小高庄,宋书玉。”宋书玉是他的母亲。
记者:您怎么能知道,那个开会的就有大陆来的学者,您也不知道吧?
高秉涵:不是,那时候知道。台湾当局对我们出席的人行前开了一个会。说是这次有中共的代表,对中共的代表免得中毒,免得跟他们交谈,有“六不”。
记者:正常的交往都不许?
高秉涵:都不许,而且是大家互相监视。
记者:那就奇了怪,您还偏要带一封信过去?
高秉涵:我想有一点冒险吧,因为没办法,信出不去,怎么办,我要告诉我的母亲,我还活着。
记者:三十年过去了,您最想知道关于老家的什么事,关于娘的什么事?
高秉涵:我就是看我母亲还活不活着。
记者:但是人家说了有“六不”,只要这信出去,一定是违背这“六不”的。
高秉涵:那当然了。
记者:怕不怕?
高秉涵:当然担心这个信没有出去。
记者:还是怕是吧?
高秉涵:还是怕。信最后原件寄到美国去,寄给我的一个美国的同学。由美国的同学从美国寄。上面没有提到我在台湾了,我从美国寄,我也怕母亲知道还有后遗症。
第二年,也就是1980年,高秉涵收到了第一封由山东发来的家书。这封信是经香港,寄到台湾的。发信人是他的大姐高秉洁。
记者:您还记得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这种心情吗?
高秉涵:其实我收到这封信,我没有拆,当时我不敢拆。
记者:怕什么?
高秉涵:怕这个信里边,我走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就不好,不在的几率很大。但是我要拆开信了,真的她不在了,那我就永远看不到母亲了,我要不拆,我反而永远有个希望,我就没有拆,我太太说你大陆来的信,你怎么没有拆。
记者:不敢。
高秉涵:我说了,考虑一下,明天再说。
记者:几天之后拆的?
高秉涵:第二天晚上。
记者:这一宿能睡得着吗?
高秉涵:抱着信睡觉的,第二天睡不着了,是礼拜天,我就把信拆开了,看了第一段,母亲走了。下面我就没再看,下面的我就没再看。
记者:娘没了,这个消息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?
高秉涵:一切思念都是空白的了,都是空白的了。
同乡聚会共分家乡泥土一汤匙锁进保险箱
一汤匙分七次喝下
没有了母亲,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。他把对娘的思念与故乡连在了一起,为此,他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。1982年,曾经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山东菏泽老乡卞永兰女士回大陆探亲,路经台湾,很多同乡希望她帮东西,但高秉涵却恳请她带一些家乡的泥土回来。
记者:有多少人托她办事?
高秉涵:几十个。我一看,我不要叫她再做什么了。
记者:为什么?
高秉涵: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,她太累了,没办法做这么多,我说我想家,想妈妈,就会想到土地,故土,是我们心目中落地生根的地方,带一点泥巴,带一点泥土吧。
卞永兰女士的那次大陆之行,从菏泽带来了整整3公斤泥土。她回到台北的第二天,高秉涵迅速组织在台湾的菏泽同乡聚会。会上他提议把这些家乡泥土分给大家,这个提议得到所有人的赞同。直到今天,高秉涵还清楚记着,当时分土时的场景,所有人都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着,四周静得“连落下一颗尘土都能听得见”,负责分土的人就是高秉涵。

记者:您怎么知道大家都需要?
高秉涵:我认为大家需要土的这个情绪,要比吃那几个枣要来得浓。大家鼓掌,说高秉涵是律师,是讲正义的,公平,由他来分。一户一汤匙,要用筷子弄平,只能凭菏泽的身份证领。
记者:多少人分这一坛土?
高秉涵:大概有五十几户,有上百人。
记者:外人肯定不能理解你们这么做。
高秉涵:我讲好的,只有高秉涵多分一瓢,因为高秉涵执行分土公平,这是对高秉涵的报酬。
作为“分土人”,高秉涵得到了两汤匙泥土,他将一汤匙泥土锁进了银行保险箱,与太太多年来积攒的金条、金饰放在一起。而另一匙泥土,则成就了一场连续七天,抚慰思乡之痛的仪式。
高秉涵:这另外一瓢我分七次把它喝掉了。我喝的时候都是晚上,十点多睡觉以前。
记者:为什么选那么个时间?
高秉涵:因为我喝泥土的时候,我想我一定很痛心,很激动,我想喝了以后就闭着眼睛睡了,免得儿女看到。
记者:不想让他们看到。
高秉涵:不要影响别人的情绪。我喝第二天、第三天,我女儿到下面来找东西,我那时候正在喝那一杯泥土,女儿一看我在掉泪,爸爸你怎么喝水在掉泪?我跟她讲我说这个是菏泽的泥土,我说我在喝菏泽的水。女儿就去给我拿了毛巾。
记者:您指的是您女儿能理解这么做。
高秉涵:她理解,后来每天晚上十点钟,女儿拿毛巾给我。
1987年10月15日,随着两岸交流日渐增加,台湾当局宣布,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。1991年5月,高秉涵首次重回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。
记者:我们从小就背一句古诗,叫少小离家老大回。
高秉涵:的确,近乡情更怯,只有像我们这样的,原来是没有希望回家的人,突然有希望回家了,才真的有这种感觉。
记者:怕见到什么?你不是连它一根草都想吗?
高秉涵:第二天一早还下了小雨,我弟弟讲再雇一个车,到我那个小高庄,大约还有三十华里,下了小雨走到半路,我叫那个师傅开快点,恨不得一步到家。但是弟弟讲了,大哥前面那个树林里面,那个就是我们的老家高庄,马上到了。我一听马上到了,心脏跳动加快,马上就感觉到浑身有点发抖。原来我叫那个司机开快一点,后来叫他慢一点。
记者:司机还得想,你到底是想快还是想慢。
高秉涵:那个司机就笑一笑,回头说你刚才叫我开快一点,下着小雨因为又不是水泥路,是泥巴路,路又不好,开车就跟划船一样,你叫我快我不能快啊,太快会开到田里面去。
记者:他哪能理解您当时的心情?
高秉涵:对啊。
到了村口,高秉涵却不敢走进去,半个小时才终于迈开了脚步。
高秉涵:到了村东头,我弟弟讲,我们先不跟你,大哥你自己先走,你转一圈,你认认看
,我们老家是哪一栋房子,你还认不认识,我们的井在哪里,我们的碾在哪里,你看一看。因为我穿的是西装,我就从东头走到西头,这个西头的井边上,有几个老人在那里抽烟聊天,他看我东张西望的,他说先生你找谁。
记者:这是乡音听着耳熟吧?
高秉涵:对,我想找谁我也说不清找谁,因为我不知道有人突然问我找谁,我说我找高春生,因为我小名叫春生。
记者:找自己。
高秉涵:这位老先生讲,高春生,他死了好多年了,死到外地了,我说高春生死了,死了。
记者:自己回家了,结果回家听到人家村子里面的人说你早都死了,这心里什么滋味啊?
高秉涵:又痛心又好笑。
高秉涵:我一看这位老先生很像我的堂爷爷,他的大名我不知道,他的小名叫三乱,我说三乱在不在?他说我就是,你是谁?我说我就是高春生。“哎呀你还活着!孩子你还活着!”我们两个就抱起来了。
记者:你说这招呼打的。
高秉涵:你刚才问我,近乡情怯。怯什么,不知道,莫名其妙。这个只有无望回家的游子,偶然有回家的机会才有这个感觉。
背负嘱托 带上百坛同乡骨灰“回家”
正是因为体会到思乡之苦,高秉涵理解那些和自己一样,在台湾漂泊半生的老人,都怀有和他一样的回乡之梦。所以,他想尽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梦想。在台湾,高秉涵成为一些菏泽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。有好几次,他被紧急叫到医院,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,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。
高秉涵:去年有个老乡96岁,双腿因为糖尿病截肢了,住在医院,从医院打电话来,医生跟我讲说,他心脏随时会停止,你是他的紧急联络人,所以通知你最后见他一面吧。我一到医院,我一看到是朱大哥,他的眼睛都不动了,就瞪着眼睛,我马上握着他的手,我说朱大哥,我说你放心,我一定陪你回去,他的泪就掉出来了,我马上用手把他的眼睛给他捂住,我说不要哭,老弟绝对会实现我的承诺,我会办得很好,不要哭。我就把他眼睛捂住,他的眼睛闭住了,这时护士和大夫也在掉泪,说高先生,他就是等你来,你说带他走,他脑子很清楚,他就走了。
记者:您最后有没有带他回来?
高秉涵:回来了。
记者:送到哪了?
高秉涵:就送到济南。
随着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,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。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,至今,他已带了上百坛骨灰回家。高秉涵说,等他自己百年之后,他希望孩子把他的骨灰,也带回故乡,安葬在自己娘的身旁。为此,以前从来不过生日的高秉涵,在自己80岁的时候,过了生日,许了愿。
高秉涵:所以我在80岁生日的时候,我太太,我的小儿子从澳大利亚也来了,他就说给你过个生日吧,80岁了,我说好吧,就买蛋糕,点上了蜡烛,叫我许个愿,但是这个许愿是不讲的,在心里边我许愿就是,尽快能够看到母亲。
记者:80岁?
高秉涵:80岁,尽快能够看到母亲。
记者:您这话什么意思呢,80岁,十几岁就没见着?
高秉涵:就是唯一的一个希望,这是每天都要想到的一件事情,后来我太太问我,你许愿,你写的什么,我说想娘,我太太马上掉泪了,你看你80岁了,还是不忘娘,不忘了要回家。
记者:您现在80多岁,自己都活成老者了,您最想和母亲做什么是没做的?
高秉涵: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我说对于“孝”我交了白卷。
记者:有太多想做的事了。
高秉涵:我有太多想做的事。孔子有一句话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,孝至始也。”孝至始也就是做个孝子,最起码要做到把你的身体保护好,因为这是你父母留下给你的。孔子第二句话“立身行道,扬名后世,以显父母,孝之终也”这是孝的最高点。但是我那个文章里面,我说我交了白卷,在嘘寒问暖这一方面我交了白卷,没有机会。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已经尽孝了,因为我把这个孝移转给社会,我孝顺了这个社会,孝顺了这个家国,我的孝顺让父母地下有知,他们会含笑九泉,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教书的先生,都是教人家如何孝,所以说我的行为,让我的父母扬名,显耀了我的父母,所以我尽孝了。
“文化这个东西,断不了的,我有这个信心。”
高秉涵曾为自己的一个孙女取名为佑菏,意思是保佑山东菏泽之意。他还在台湾创立了菏泽同乡会,并被推选为会长。同乡们一起为家乡捐资筑路,捐赠图书,设奖助学。传统文化、家国情怀支撑着80多岁的他在两岸之间往来奔走。而这次带着孙辈的回乡之行,反而让他多了一层对未来的牵挂。
高秉涵:你看我的小孙女,我那天问她,我们的国家最长的一条河是什么,是淡水河。
记者:您设定的答案是?
高秉涵:我本来以为她说的是长江和黄河,问她长江黄河,她说那也不是我们台湾的。他们也不说台湾是国家,他们没有那种观念,她就是台湾人。所以我心中很苦,所以我说不堪回首这四个字来形容我,是很恰当的。
记者:您觉得这种状态能改变吗?
高秉涵:我认为虽然是这个文化台独,让孩子一个个都这样想,但是我总有一个信心,文化这个东西,你想去掉,等于血管里的血,你想把你父母的血整个换掉不可能,端起碗来拿筷子这就是文化,食文化,开口讲的中国话,讲的福建的方言、闽南话。
记者:您的意思就是说?
高秉涵:文化这个东西,断不了的,我有这个信心。
| 

79924a9a-69f5-44ea-b859-9d9b24f0a3f8.jpg)
f6befb5c-fd59-4755-81b1-72f75dec4e6e.jpg)
5cc42da7-5964-4185-b6d9-f79e919f06c3.jpg)
d9b4cc93-1e83-41e2-97e6-609175753d02.jpg)
74a6204f-3074-4c8e-b1d0-461a2861fec6.jpg)